这个“痞子”,竟以0分考入中央美院,高调请辞清华教授,屡屡得罪财团名流,他怼天怼地的背后是为了什么?!
他是至今唯一以英语0分的成绩,
考入中央美院的学生。
但他却并未珍惜,
还说自己副业是画画,
主业是撩姑娘,
老师说他是“会画画的臭流氓”。
他受清华大学特聘,任教授和博导,
但却毫无留恋,高调请辞,
同事说他“又傻又无情”。
他最擅长的就是得罪各种财团,
笑谈余秋雨“身有官臭”,
还评价于丹不过是个“大学辅导员”,
世人说他“太张狂”,
他却笑答,“我本就不是个好人”。
但今天,
他的名字却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晓,
他的言论如春笋初剥,
一层层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爱他的人极爱,
连他骂的脏话都能听出韵味;
厌他的人又极厌,
仿佛他一张口便已经错了。
而他,
却对一切都毫不在意,
在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,
在怼天怼地的不屑背后,
原来,
他秘而不宣的心思里藏着这样一个秘密……
他,就是陈丹青。

1953年,他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弄堂。
爷爷陈砥中是黄埔军校学员,
父亲陈兆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,
能写会画,父亲因喜爱文天祥,
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诗句,
便为他取名“丹青”。
打小儿他便在家中,
熏染了一身的文艺气息。
他的童年,无忧无虑,
偶尔还跟着长辈吟诗作画,
过得很是惬意。
而时间来到了1970年,在他16岁时,
生活正式向他颁发了“成人礼”。
父亲被划为“右派”,母亲也未能幸免,
年少的他也被扣上了“富反坏右”的罪名,
家中的书籍、画册全部被毁,
他的上海户口也被一笔勾销,
随后就被下放到赣南与苏北,
去条件最恶劣的农村插队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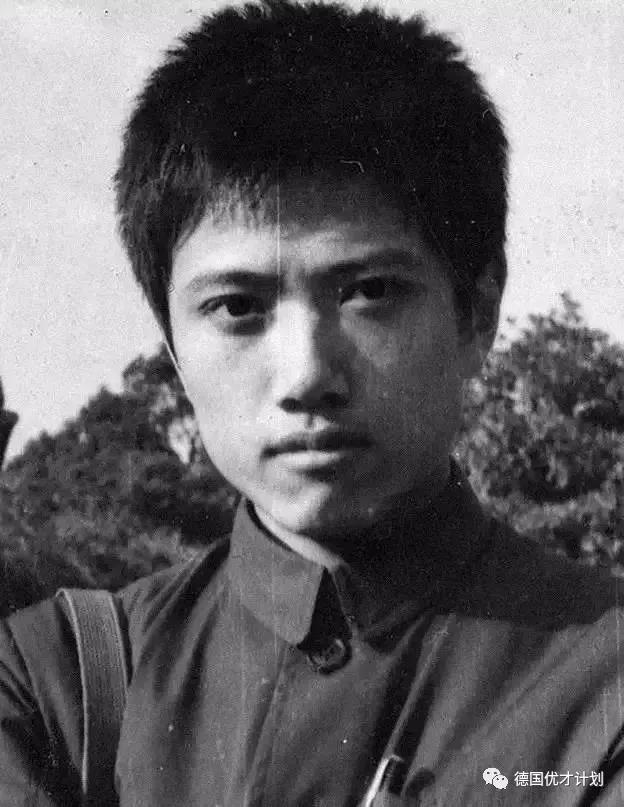
对于没有过多精神追求的人,
农村的生活或许还没那么难熬,
但是对他来说,每一天都是折磨。
没有书、没有画册,
没有任何精神寄托,
他回忆说,“那时很绝望,
每天都是黑色的,3个人挤一张床,
老鼠在被子上乱窜,
心里很绝望,脑子是空的。”
为了不被枯燥的劳动生活逼疯,
他就在收集的火柴盒上画画,
一画就是三年。
就这样,1973年,
他居然出了《边防线上》
《飞雪迎春》等三四本连环画。
公社的领导偶然间看到了他的小画,
认为他很有天赋,堪当重任,
便大笔一挥,
送他去了一个重要岗位:
骨灰盒厂。
从此,他就开始每天画骨灰盒,
几年下来,他竟画了整整一千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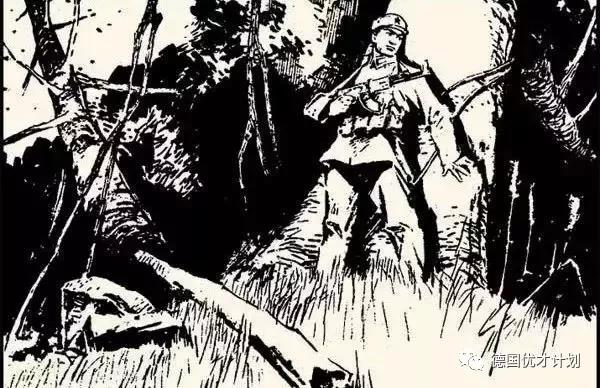
陈丹青创作的连环画封面《边防线上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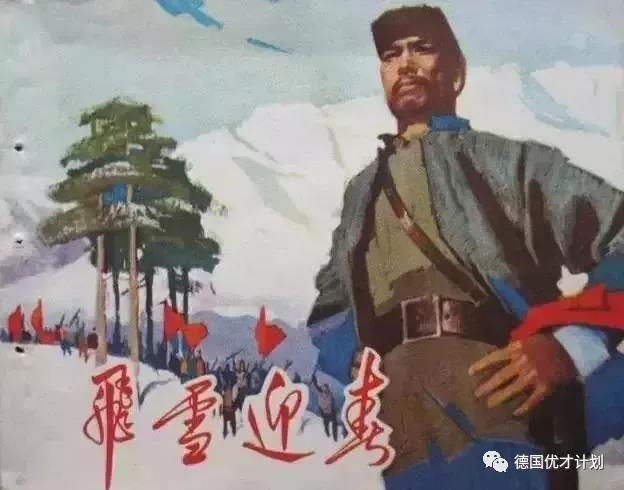
他的笔法细腻而生动,
在当地渐渐的小有了名气,
但他怎甘心一辈子都在骨灰盒上画画,
于是拼尽全力争取回城的机会。
终于,在插队6年后,他等到了一个机会,
一步步的过关斩将后,
他终于被南京商业局录取了,
可最后,都已经过了体检环节的他,
却在报道前夕,被一个关系户顶替了。
那一年,22岁的他仰头望天,
伸出了中指,
从此,便开始了怼天怼地的人生,
一切都预示着他未来不再平静的生活。
看清了自己没钱、没关系的现实后,
他明白,要想改变命运,
只能靠自己这双能画画的手了,
于是,便一门心思专攻绘画。
先后他的作品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、
《进军西藏》等大型油画,
在南京艺坛上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

泪水洒满丰收田

进军西藏
1978年,高考恢复,他即刻抓住机会,
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。
但跟别人不同的是,
他的英语试卷上赫然写着0分,
至今,那份试卷上还留着,
他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:
“我是知青,没上过学,不会英语!”
年少气盛的他当时一定想不到,
后来他的人生竟会与这英语考卷,
牵扯出理不清的爱与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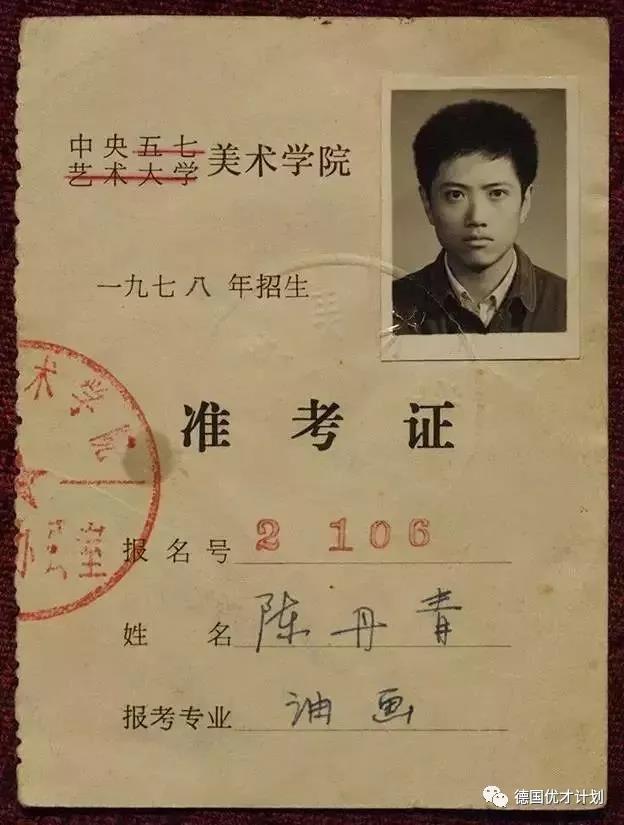
陈丹青的准考证
由于他的绘画功底实在太深厚了,
导师惜才,最终还是破格收他入门,
之后的几年,他在中央美院里,
交出了人生中第一份初显锋芒的答卷:
《西藏组画》,
组画中的七幅油画分别为:
《母与子》《牧羊人》《朝圣》《进城之一》
《进城之二》《洗头》《康巴汉子》
后来被约定俗成地统称为《西藏组画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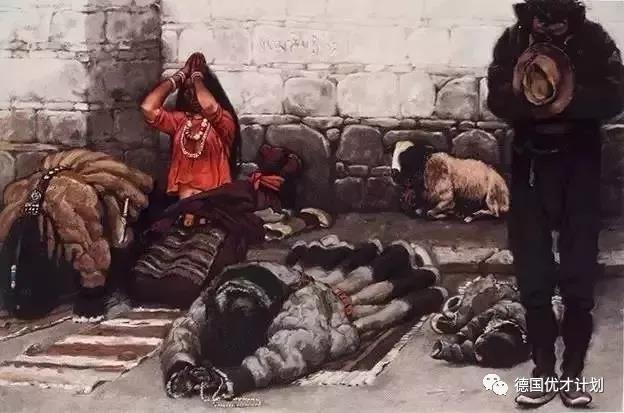
朝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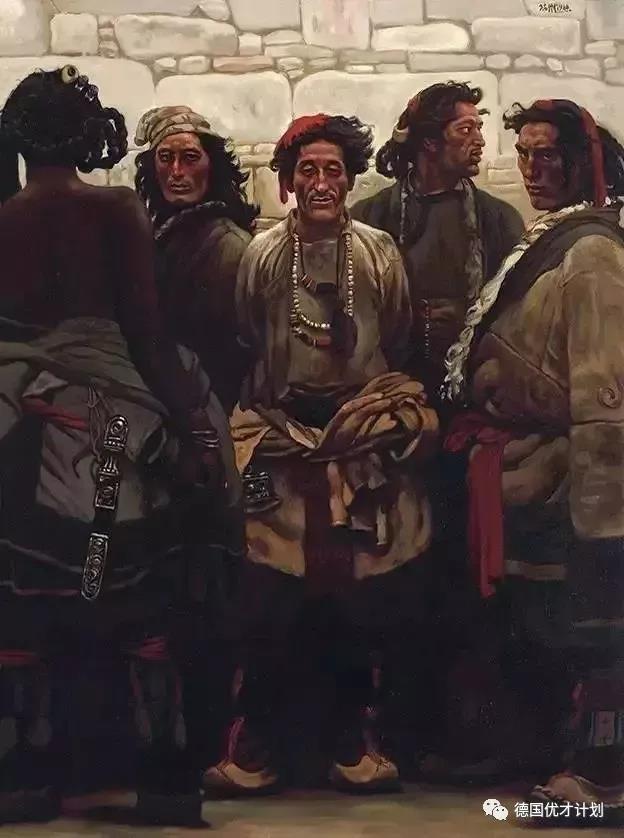
牧羊人

进城之一

进城之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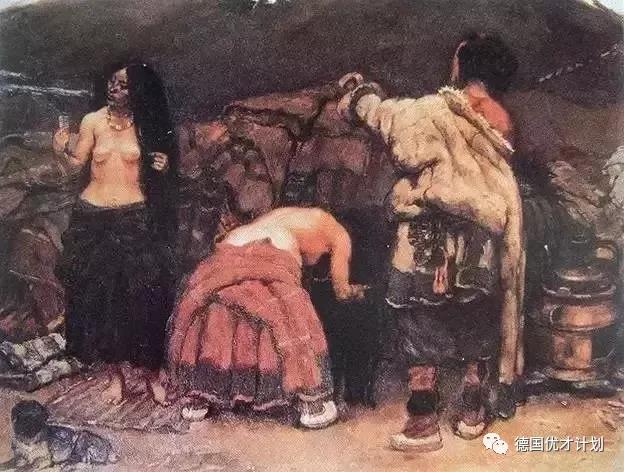
洗头的藏女
《西藏组画》放弃了中国当时,
传统的苏派绘画风格,
而是采用法国学院派画风,
以前从未有人这样画过西藏,
这让当时中国的美术界耳目一新,
所有的文艺报刊都争相刊发与评论他的作品,
这组画让他迎来了,
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,
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。
而他不但是个画家,还是个作家,
还出版过一系列的文学作品:
《纽约锁记》《多余的素材》
《退步集》等十余部书,
涉猎社会、艺术、文化、教育等多个层面,
写作也成了他在绘画外,
对社会的又一巨大影响。
80年代,
春风得意、崭露头角,不羁自由的他,
没日没夜地和朋友们“瞎玩”,
他说:老有人来问我,你是怎么成功的?
妈的我没想到成功,我画画,因为我喜欢。
我不记得小时候有过“成功”的说法,
成功观害死人,你要去跟人比,
第一名还是第二名......
我对一切需要“比”的事物没有反应,
我画《西藏组画》时,
就是为了远离当时的“正确”。
而他还想离得更远点,
他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,
听说那里有圣殿,是艺术家的天堂。
于是,他放弃国内的一切,
只身一人来到了美国。
而让他没想到的是,
在美国他没遇见天堂,却遇到了木心,
这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人。

陈丹青(左)和木心(右)
1983年,他结识了木心,
两人一见如故,
常常彻夜聊天,结伴出游各国。
木心曾教他:
“人的修养不在于学识的多少,
而在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。”
有一次木心和他一起去餐馆吃饭,
邻座坐了两个老外,
他说邻座是意大利人,
上去一问,果然被他猜对,有点得意。
可木心说:“你刚去过意大利,
你想证明你的虚荣,人难免会这样,
但要克制,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。”
这就是木心教会他的:
“修养是很具体的,就是一件件小事,
哪怕失了一句话,也是失了修养。”
他在木心潜移默化的影响中,
重新审视自己,也重新审视中国。
他说: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参照,
我在美国看见每件事情都会想到中国,
所以我跟人说出国不是为了去看国外,
其实你会看清自己。
终于,游历世界后的他,
决定回到祖国,
想用一己之力为中国大地绘上一笔颜色。
但他却不曾预见,回国后的他,
却在舆论界掀起了巨大的惊涛骇浪!
2000年,
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,
担任教授和博导,
但清华的招生制度却一次次打击了他。
曾有一个极有天赋的女学生,
由于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,
女生问他,“老师,请问画画搞艺术,
非得英语好吗?”
他想到自己曾经0分的英语试卷,
竟无言以对。
后来,这个学生先后两次,
都是由于英语不过关而被清华拒收,
最后,只能转往英国继续深造。
得知消息后,他痛心疾首,
失去好苗子对他的打击太大,
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英语不及格,
但却幸运考入大学的自己。
而后,很多天资过人的考生,
由于英语或政治被拒收的情况屡屡发生,
他爱才惜才,想全部收入门下,
但学校有规定,不能破例。
谈起这样的招生制度,
他愤慨不已说:“齐白石会说英语吗?
黄宾虹会英语吗?
画画非得要英语好吗?
专业前3的考生永远都进不来,
只要英语不及格,
他们的画就像废纸一样被丢掉。
我不能忍受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,
把这样一些有才华的孩子拒之门外!”
于是2004年,他递上了辞呈,
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清华美院。
临走时,他说:
“不从众,保持独立人格,
坚守个人的价值观,这在中国,非常难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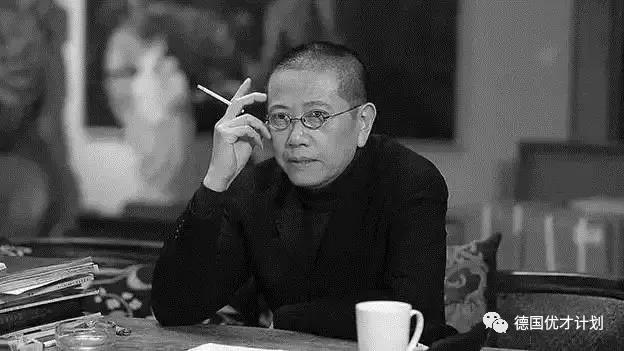
面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,
他没有委曲求全,没有安于现状,
而是毅然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,
成为反对刻板、迂腐现象的先行者。
此后,脱离了体制的他,
更是像是笼中被放飞的山鹰,
发出的言论愈来愈激烈,
一次次刷新着社会的关注度。
有人问他,怎么看待中国的教育?
他说:
“中国若体制不变,我此生不会参与教育!”
有人问他,中国最缺乏什么?
他说,
“最缺教养,整个民族都缺。”

陈丹青自画像
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纯艺术者,
精神世界是一间无菌室,
而现今社会中的浊气杂流又太多,
他只能选择一一回绝,针锋相对。
用他的画笔、用他的言论、用他的思想,
给这喧嚣甚上的尘世间,
抹上一种纯粹的颜色。
无数的媒体、集团邀请他,
希望他能“立公心、谈公论”
而他却常常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
经常反其道而行之,
完全不按照预设的台本来讲,
常搞得主办方灰头土脸。
比如在某次古城建设会议上,
主办方是个大财团,请他去给撑场面,
说几句“漂亮话”,渲染一下文艺气息。
结果,他却毫不留情,
说到激情处,干脆扔了台本,
慷慨陈词,说道:
“我们正在毁灭这座古城!”
“不是因为战争,而是因为建设,
古城被毁了!”
“贵集团已经做了很多,
但我看,还是少做一点的好。”
这一下,就把大财团给得罪了,
他却还若无其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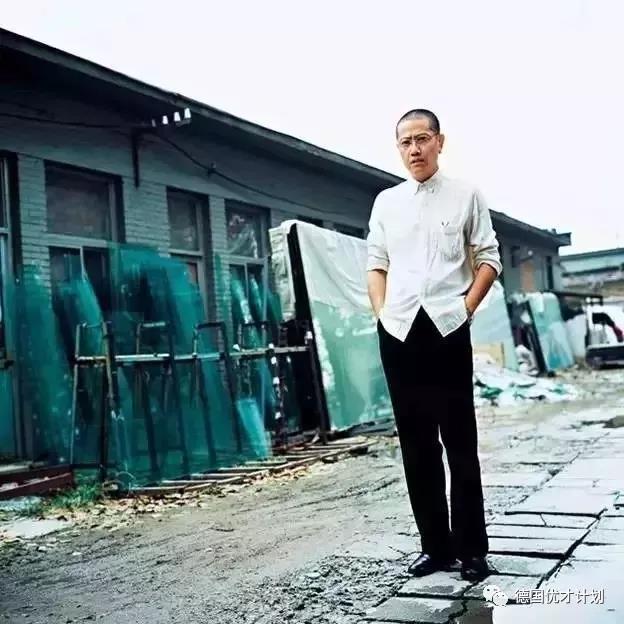
不单是对企业、财团出言不逊,
对社会知名人物他更是毫不客气。
信马由缰,直抒胸臆。
人家说,余秋雨是现代文化学者的典范,
他却说:
“余秋雨首先是一个官员,
其次才是一个学者”
人家说,于丹老师佛口莲心,语意深远,
他却说:
“于丹其实就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大学辅导员”。
有人说:陈丹青这个人真傻,
竟说些有智商没情商的大实话。
而他好像从来就不怕得罪人,
随着他“过激”言论越来越多,
社会上批判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
但他却硬不低头,也永不合作。
身边的朋友劝他,
从众一点,看开一点,随世一点,
但他偏不,他说:
“我本就不是一个好人”。
但是,
与他批判社会名流的狠辣相反,
对待年轻人和社会上的弱者,
他却和蔼可亲,毫无架子,
颇有儒士之风。
他常鼓励年轻人,不要怕错,
不要自暴自弃,要勇于尝试。
他说:有人以为没上大学很自卑,
有人以为上了大学很牛逼。
其实,上没上大学,上哪一个大学,
都不重要,重要是,
你没上大学却没有放弃自己,
重要的是上了大学你在干什么。
再好的大学也有渣子,
再烂的大学也能出人才。
不是大学决定你未来,
而是在什么样的大学,什么样的环境,
你都知道你要成为哪种人。
而对待女士,他一向绅士,
饭桌上会为女士们倒水、服务,
很体贴,话也不多。
在生活中,他更是清透,
多年来,一个绯闻都没有。
也许正是由于他知道自己坚持的是什么,
才能在这喧腾的浮世上,
守住一种执着的态度。

而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,
他更愿意当一面镜子,
映出社会最真实的一面。
他抨击大学教育,
抨击野蛮拆迁,
抨击医疗系统,
他说:
“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,
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?!”
他说:
文凭是为了混饭,跟艺术有什么关系?
单位用人要文凭,
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,
文凭是平庸的保证,
他们绝对不会要凡·高。
他说:
“作为一个中国人,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”
他说:
“中国人的通病,就是做事不踏实,
做人不老实。”
他说:
“社会的缝隙正被商家与政客占满了”
他说:
绝大多数中国人草芥般生出,
草芥般死掉,农村更不必说。
他说的义愤填膺,说的情真意切,
说的无比焦急,
说的时而绝望、时而期望!
他说,
“我看不见中国学生的英语如何,
我只看见了大家的中文一塌糊涂”
他说:
“中国的文艺就像中国体育,
表面上看,满世界的拿金牌,
可是社会上哪有体育?”
......
因为敢于如此直言,他得罪了很多人,
更是站在了当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,
许多人在他背后放冷箭、中伤他,
但他却还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
也许真如那句话所说:
“真正的勇士,不是敢于直面风暴,
而是在背对风暴的时候,
依然能气定神闲。”
而他,正是这一种人。

我们都知道当前社会上的问题,
都知道想要进步,就需刮骨疗毒,
刮骨很痛,治疗不易,他知道,
但他更知道,
讳疾忌医的结果只能是更惨痛,
集体失声的国家会有多可怕!
所以,他想揭开国人的疮疤,
想掀开每一个伪善的面具,
想一瓢冷水浇醒这虚于浮华的泱泱社会。
他不羁言论的背后,他焦灼痛斥的内心,
隐藏着一颗急于报国的文人真情,
他想要的,不是个人的功成名就,
而是拯救整个中国、整个社会,
原来他秘而不宣的心事里,
藏着的就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秘密。
也许在他心里,
在父辈一袭长衫的民国中,
祖辈四书五经的经纶里,
都还牢牢的孕育着这样的家国真情。

现在的他,戴着一副圆框眼镜,
讲话慢条斯理,
不说话的时候微微笑着,
沉稳中透着睿智与随和。
当人们以为他怼天怼地的时候,
一定是很气愤的,而他却说:
我几乎从来不生气,因为我认为没必要,
有问题就去解决,
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,
但我不生气,不代表我没脾气,
我不计较,不代表我脾气好,
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,
我可以告诉你,我并非良善。

唇舌似剑,画笔如刀,
长衫一袭显风骨;
颠沛半生,归来故里,
评是论非为初衷。
丹青之心,铁血之意,
画里话外皆是情;
悲洒古今,快意人生,
甘为国人背声名!
这样的文人墨客,
不正是当今繁华乱眼的文学界中,
一股清冽的山泉吗?
这样的毒舌议客,
不正是我们这谨小慎微,
言不由衷的社会所最缺的吗?
他的话值得当下我们用心去聆听,
他的嬉笑怒骂值得当今社会为之深思!
上一篇文章:吴冠中画春,给你一个最美的江南!
下一篇文章:青州山水美如画,他带你游山玩水